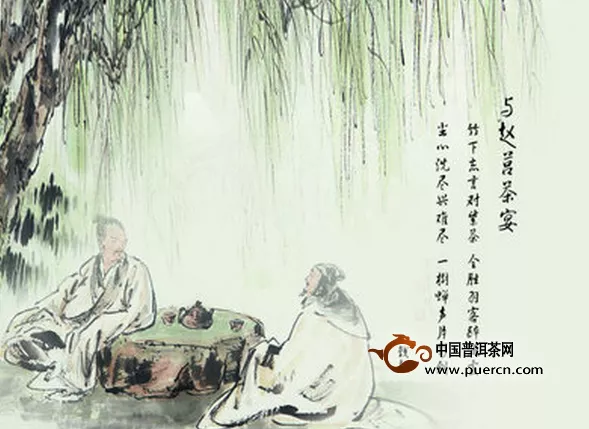
因为喝茶,不免留意与茶有关的事情。特别注意到茶的成为举国之饮,文人在其中的推波助澜。
元稹有一首一字至七字《茶》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除了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概括以外,特别提到了“诗客”和“僧家”。唐之前,有关茶的诗文极少,中唐以后,以茶入诗大量增加。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这类旷世的酒徒,也无不嗜茶,无不遗有诸多茶诗。很显然的,唐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与其时场面上和山林中的达士名流或诗或文的赞赏不无干系。
这些茶诗,直接和间接地几乎涉及茶叶作为产业和文化的所有方面:
“倚溪侵岭多高树”(杜牧),“尧市人稀紫笋多”(释皎然),“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许浑),“三军江口拥双旌……水门向晚茶商闹”(王建),“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讲的是茶叶的收购、运输、贸易,使荒野变成繁荣的集市、军营变成茶樯林立、茶商喧闹的商埠,使商人抛下哀怨的令大诗人泪湿青衫的妇人。
“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湖州紫笋来。”(张文规),“动生千金费”,“所献愈艰勤”(袁高),讲的是宫廷贡焙。
“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皮日休),讲的是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形成起来的茶具,不再是早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那样的平常饭碗或汤碗。
“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释皎然),讲的是由客坐敬茶而兴起的茶集、茶宴、茶会以及有明确目的和主题的社交活动。鲍君徽、王昌龄、钱起、李嘉祐都详细描写过这种饮茶礼仪。
“或饮一瓯茶,或吟两句诗……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白居易),“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孟浩然),“水淡发茶香……钟声振夕阳”(刘得仁),“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杜荀鹤)……《全唐诗》凡提及茶事的诗词中,僧道写作或诗人们在寺院和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之近二。文人与僧道不单是嗜茶者和茶的鼓吹者,也是茶艺和茶道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茶与酒同为国饮,酒易乱性,茶为养性;饮酒尽可豪放,人皆呼作英雄,饮茶则宜雅致,否则难免“牛饮”之讥;醉酒固然造就了大诗人,也惹出了许多麻烦。虽然也有“醉茶”之说,却没有听说过醉了茶在茶楼题反诗的。“脑如冰雪心如火,舌不饾饤眼不花。协力免教天下醉,三闾无用独醒嗟”(郭沫若)。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茶的“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正对了文人们孤芳自赏的胃口。茶之为道,在“和、清、敬、寂”四字。此其所以西人认为茶“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是人类的救主之一”,“是伟大的慰藉品”。而唐人诗文推崇的“和、清、敬、寂”则成为后来的日本茶道的要义。
丰富多彩的茶诗“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吕岩),文人们在把茶宣传成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上品之饮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的精神意义,使饮茶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升华为高尚的精神享受,成为艺术和哲学。
大约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时下许多茶叶产地大办“茶文化节”,邀请专家文人听茶歌、观茶道,品新茶、谈茶经,以茶会友,以书会友,以诗会友。倘旨在经由对茶的文化品位的追求,促进对茶的自身品位的追求,自然是有远见、有胸怀之举。也见有以为“功夫在诗外”的,过于急功近利,视文化作纯粹的产品广告,只求推销本地本企业茶叶,则恐怕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事与愿违。
有感于这类的大轰大嗡,我不揣浅陋地在一次“茶文化”盛会留下这样一副手书联句:
竹露松风蕉雨
茶烟琴韵书声
希望在一个喧嚣躁动的世界,至少在与茶有关的事情上,能多少保持一点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