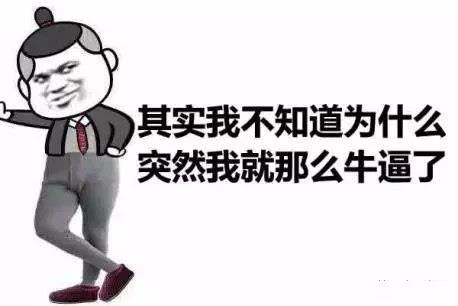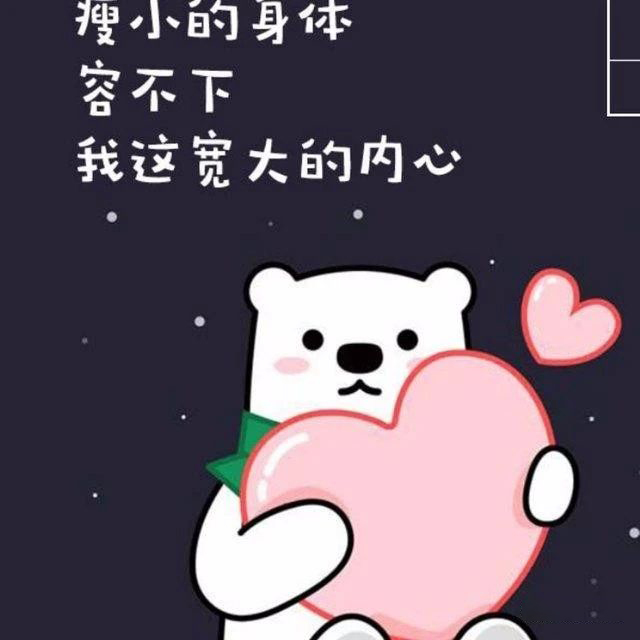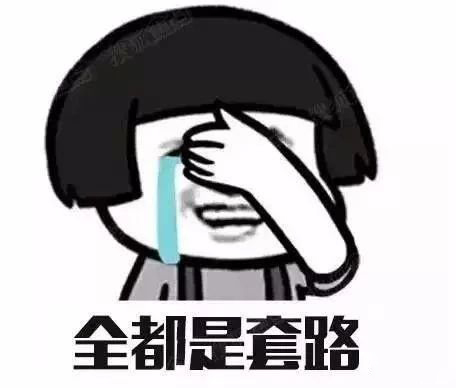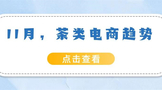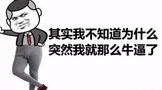我生活在了一个爱茶的城市,鄂西北的一座小城--老河口。这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城市,茶馆却多得数不清,且不说大街小巷走几步就有一个茶馆,就连只有上十户人家的偏僻角落,也赫然会有一家茶肆。茶对于这个小城市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嗜好,而是生活的必需,是一种深迷其中的瘾。每天早上,许多人一起床,来不及漱口洗脸,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泡茶,不喝足了瘾,是不会想到去干别的事情的,只有喝过了瘾,才感到全身通泰、舒服、有精神气儿。喝足了茶,开始出门,但不论是去上班,还是出去早锻炼,或是出差旅游,都
不忘带上一个玻璃杯儿,里面酽酽地泡好一杯茶,走几步就会拿出来呡一口。

你无论是到哪家串门或是到哪个单位办事,主人打过招呼,首先转身去给你泡茶,一般的人都会随及拿出自带的玻璃杯申明道:“我带了茶”,但热情的主人还是会说:“我给你重新沏一杯吧!”或是说:“我这里有好叶子,来,尝尝我的”。
逢什么部门开什么大会,是可以不准备茶杯的,因为到会者一落坐,就都会随手从提包中拿出已经装好茶水的玻璃杯来,会议筹办者只需准备充足的开水,也可以不请服务小姐专门倒茶水,只需在每桌子上放一瓶开水即可,在续茶水上,人人都是自觉自愿自己动手的。
这里的人们娱乐休闲也大都会去茶馆,或在茶馆聊天,或在茶馆打牌搓麻将,或在茶馆看戏听曲,就连朋友中的聚会和相亲也往往选择在茶馆,茶馆是这里永久时兴的活动场所。
因为家家都嗜茶如命,所以恋爱中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中时,是必须带两斤茶叶去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懂规矩,不知礼数,婚事就可能会泡汤了。结婚后的女婿每年逢十五、中秋、端午节到老丈人家去时,所带的礼品也必须有好茶的。不仅是新上门的女婿,平常亲友逢年过节的走动,送茶叶也是胜过酒或其它礼品的;就连单位每年夏天发放的防暑降温品也一律是茶叶。因为喝茶,小城的各种有奖活动的奖品和一些单位的馈赠品也大都是各式各样的茶杯和保温杯。
久在茶水中浸泡,小城的人个个泡成了“茶精”,只要看一眼茶叶,就能辨出是新茶还是陈茶,是春茶还是秋茶;闻一下茶叶,就能估出这茶值多少钱一斤。想以次充好,以便宜价进,想卖个好价钱的茶商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就来也怪,这座对茶情有独钟的城市是不产茶的,它的乡村有上千平方公里,却难找得到一片茶园。不产茶的地方为何喝茶成风呢?笔者沿着这座小城的历史足痕去寻找,终究发现了小城人酷爱茶的渊源——
老河口地处鄂、豫、川、陕四省交汇的咽喉地带,又处在汉水中游东岸,而古代和近代交通与运输主要是靠舟楫。从清朝中期开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埠,从汉水上游秦岭巴山运出来的桐油、核桃、木耳等山货要在这里起坡,转手交易后再运到河南中原一带,或再顺江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来自中原一带的粮食、棉花又通过老河口的帆船上运到汉水上游的郧阳和安康山区,下运到汉口;到了近代,汉口的工业品如洋油、洋皂、洋糖、洋火又通过汉江运到老河口交易,再转运到中原和陕川的一些山区。到清末的时期,老河口的商业繁盛超过了附近的襄樊、南阳,平常往来的商船在老河口的江面上桅帆林立,有上千艘之多。南来北往的商人纷纷驻足于此,为了便于商贸的接洽,逐渐出现了茶馆,商人们都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到民国初期时,老河口的茶馆达到鼎盛时期,七十二条大街小巷中分布着二百多家茶馆。
茶馆的兴起,自然带来了喝茶的嗜好。虽然,后来因航运滞后,其它交通的发达,老河口已经失去了昔日商埠的繁盛,但老河口的居民大都是商家的后代,也就大都沿袭了父辈的喝茶之风。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汤礼春(湖北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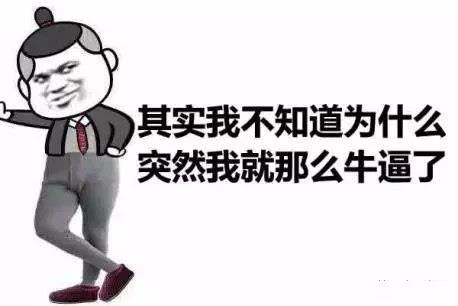
茶人列传S
S做茶十余年,有点名气,非常自负,常认为自己的茶好,别人的都是垃圾。
一日,S来到旗下的经销商小黄处,小黄是S比较看重的,打算大力培养,让小黄不再卖其他人的茶。
S没预约,店里没其他客人,小黄正好在泡茶,没换茶,顺手给S倒了一杯,S随口一喝,立马找垃圾桶吐掉,连声骂道:“什么垃圾茶,难喝死了,简直要命。”小黄尴尬极了,但又不能不回应,只得小声说到:“老师,这是你的茶。”S面不改色应到:“是嘛,我来看看”。
S占了主泡台,找小黄要来茶饼,自己重新撬茶、泡茶、润茶、分汤,只见S缓缓抿一小口,闭上眼睛回味良久,吐了口气,对小黄说到:“好茶!舒服!小黄,你泡茶的技术需要多跟我学学,我这么好的茶被你泡坏了。”接下来,S开始大谈他的茶多好,游说小黄只卖他的茶。

茶人列传T
T算是茶界老人,做茶网站,做茶报纸,一年年折腾下来,没有大富大贵,养了一帮人,老婆女儿聚在身边,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
2013年,T开始大额银行贷款,第一次就利用公司流水贷了五百万,中介先帮T买房买车,贷款下来扣掉车款房款和手续费,也有三百多万。T扩招人员,网站升级,一时间茶城到处都是T的人。最厉害的当属和人合伙做小额贷款,日进斗金。那段时间见T走路都自带风声,踌躇满志的样子,颇有些成功人士风范。
再接下来,听T说起又找其他银行贷款了几百万,开始和茶企合作做自己品牌的茶,招兵买马,风风火火很是热闹;又到处拆借和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合作,每天利息都上万进账,T买了第二张车,计划换大房子,做更高端的茶。
2016年,T开始到处借钱,据传,小额贷款公司的款一分都收不回来。
再后来,听说T车房都被查封拍卖了。那年,我远远见过一次T,瘦得不成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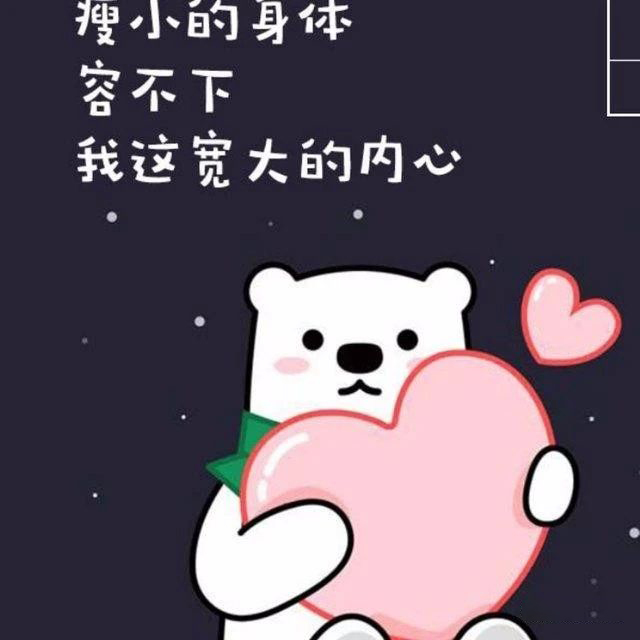
茶人列传U
2012年春,易武麻黑村,昆明的李先生转进了茶农U家,U非常热情,连忙泡茶,并吩咐老婆杀鸡做饭。
U刚做好晒干的古树茶李喝完后觉得还算满意,一问价格也不算高,李和U定了5件茶,50公斤,没付定金,李在U的本子上写了电话,说还要转转易武其他地方,也就2-3天,回去之前转进来再把茶拉走。李吃完饭带着U送的一大包茶样就走了。
李被其他事情耽误了下,过了一周多才去拉茶叶。U说你可来了,打了好多电话打不通,中途有人要买,想着答应了李,又不好意思卖,正着急呢......李边嘀咕不可能啊我电话一直开着,边翻U的本子,发现电话号码确实错了一位。
接下来,李每年都要转到U家,经常是和一帮做茶的朋友三五成群一起来,李和李的朋友们吃了U不少鸡,也买了U不少茶。

茶人列传V:美女茶艺师
你脸红什么?出来后,强哥问我。
今天强哥带去我一个茶馆喝茶,茶馆装修古色古香,室内沉香袅袅,小桥流水,古琴声声,是十分专业的老茶馆,让我这个做茶十来年的人自惭形秽。
主人是个唐服飘飘的美女,专业茶人,据说还去日本学过茶。美女引我们坐在一整套都是海南黄花梨茶台前,先从一青花水缸取水,再注入一名贵老铁壶,放在炭炉上烧水,又爬高拿下一檀木老盒,取一饼老茶,纤手轻轻撬茶,放小称上称好。
水开了,美女取出一个明青花的盖碗,注水洗茶,在我们面前摆上同样是明青花的品茗杯,美女边忙边介绍,这是市场特别稀少的一款几十年的老茶,是强哥来才从高阁取下来,动作轻缓,语速轻柔,好一个伺茶可人儿。
洗茶后,先给我们喝了杯清水后,等了十来分钟才开始泡茶。从我们进门到喝茶估计半小时吧,搞得我都有点口渴了。
美女泡茶分汤给我,我就迫不及待端起杯子,一口下去,一大股六六粉味道,又不好吐掉,憋得我脸通红。只好咽下去,喉咙痒得不行,干咳了好一会。后面就推脱今天身体不适合喝茶,
我回了强哥一句,今天天气太闷了。

茶人列传W
W是北方人,做茶多年。
春茶某日,W来到云南某茶区村,考察了一番,甚是喜欢。
W对茶农说,茶园绝对不要打农药不要用化肥,我们这些做茶的就喜欢原生态的,你去帮我组织这些生态茶,农药化肥的一概不要,W付了定金,预定了一批生态好茶。
几天后W来收货,对着茶农猛喷,怎么这么丑,茶叶子黄黄的,瘦不拉几,还有虫眼...旁边这个好看,绿油油的,粗壮,芽头大,这个多少钱...
W在村子里拉走了一整车好看的茶,价格比预期的便宜一半还多。W心满意足,打着满肚子土鸡土酒的饱嗝,说明年再来。
送走W,茶农对老婆道,还得再买点农药和化肥,把那些放养的茶园也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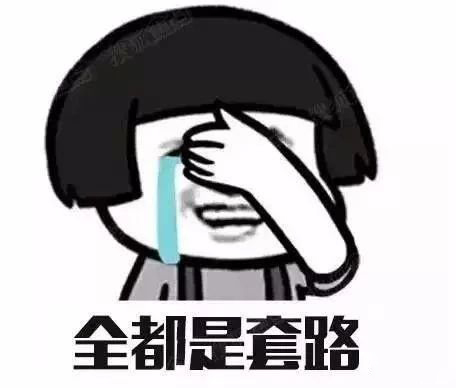
茶人列传X
X南方人,来到更南偏西的云南做茶。
X之前在老家有一小茶叶店,没啥起色,发现对于普洱茶来说,云南机会更多,就关店来到云南,不开店,长期混在昆明和版纳,顺便倒点茶叶卖。
在昆明喝茶久了,认识了版纳茶区做茶多年在昆明开店的李先生,X发现自己对茶的认知和李先生差距很大,也远无李先生的生意好,李先生周围有一大帮喝茶的资深茶友让X很是羡慕。
经过一系列的运作和巧合,X在一个恰当时机拜李先生为师,于是,李先生就变成了李老师。
李老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带X踏遍古六大茶山,把身边的人、山上茶农等各种关系都介绍给X,来客人也不避讳X。当然,X也非常给力,只要是李老师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做司机,打扫卫生,泡茶,搬茶,从不吝力气。一时间,X和李老师,成了模范师徒,清风霁月,羡煞旁人。
惜花无百日红。
李老师突然发现X不怎来茶店了,打电话让来也是经常推,就算来也是坐一会就匆匆忙忙离开。周围的一些客人好些也不怎么来茶店,店上小姑娘说听说是X自己开店了,X的茶也更好更便宜。
李老师又变成了李先生,李先生能看见X的时候一般是在茶山以前李先生引荐过的茶农家,再后来,有些茶农委婉告诉李先生,没有茶,都被X包圆了。
后来,李先生又听人说,有个大师叫X,自学做茶十几年,常年呆在版纳茶区,古六山行走,深耕多年,是非常厉害的大师。关键是非常红,周围一大堆有钱的粉丝客人。
再后来,会有人问李先生,是不是和X学过茶,要不你们两很多认知、观点是一样的,产品相似,连客人也不少都是认识的。李先生一般都正襟危坐应道,不认识。

茶人列传Y
Y是云南知名茶专家,经常能在很多茶相关场合见到Y,Y都坐重要位置,且多坐在舞台中央。
2013年,在一次茶会上我和Y碰巧挨着坐,那是我第一次见Y,之前听说过Y,茶行业知名老专家,那次我说了一些恭维的话,和Y互相留了电话。
2013年底,Y打电话给我,说了很久,我几乎就嗯嗯应着。Y来电话的意思是,以前冰岛茶还不出名的时候,他收了很多冰岛,总共有几吨,他作为大学教授,还很年轻(这一点很奇怪,那时Y已经很老了,我才30多,他怎么就年轻了?),不方便出面卖茶,让我帮出货,这些茶都是好东西,追的人很多,他个人研究茶几十年,学生遍天下,可以帮我51普洱导流量......接着说了很多,大意就是他有多牛,影响力很大,我和他合作,是我的大机会,如有意向,合作细节可以谈......
我非常反感一上来就牛皮哄哄的人,现在也是。但那次我还是很客气挂了电话,只是Y一直也没等到我的消息。
再见Y已是2015年,在某品牌茶的推荐会,Y依旧主席台就坐,我坐在观众席。推荐会请了一堆人,还有相对专业的主持人,先是介绍了新品茶,接着就是冲泡这款茶,茶艺师先把主席台等人包括Y的茶杯清空,接着泡新茶,给大家分茶,主持人就着茶艺师倒茶的间隙,请Y给大家讲几句,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Y端起空杯(茶艺师还没有给Y分茶),声音洪亮说到:“非常高兴出席这次茶会......此茶香气迷人优雅,汤色黄亮,口感清甜.....",瞬间,我耳根都红了......
后来,我几乎不参加这样的茶会,也没再见过Y。

茶人列传Z
认识Z比较久,但基本没什么业务来往。Z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勐海混,倒原料卖,经常东家原料卖给西家。我2017年开始在勐海建厂,和Z的接触就更多,Z会经常过来聊天,告诉我一些勐海的信息,顺便推销一下茶。
有次Z打电话给我,要拿一个熟茶给我喝,发酵得非常好,原料也很好,说我肯定会喜欢。我平常也知道Z到处串,说不定真能发现好东西。我非常期待在自己的勐海店上等Z。
Z到了之后,我开始泡Z带过来的熟茶,越泡越熟悉,特像我自己的第一批熟茶,我那批熟茶由于是试验品,菌香浓,汤水细软,汤色稍浑,属于特点非常明显的熟茶。到了7、8泡之后,我几乎可以确定了,就问Z是不是找L先生拿的样品,Z好生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我回到:“这就是我的茶,因为才出堆,我只给过L先生样品”。
——作者吕建锋
无论是对于一款茶的钟爱,还是对于一个人的钟情,我都随缘随喜。万物与俗尘,诸事与凡心,自然切入才最好。对于茶事,我不想刻意研习茶艺,也不汲汲于佳茗,只是如此,坐在喧嚣之外,赏轻歌曼舞,修云水禅心。

有朋友诗心荡漾,尤喜流连清雅茶室,据说经营茶室的女子,曼妙温婉,素心可人,于是,灯火阑珊,相约一路奔来。屋子里已有几个陌生的女子,于是,寒暄,落座,倒茶,我不懂茶道,只是看着,看手腕起落,茶汤清流,从未谋面,却毫不拘束,我喜欢置身这样的环境里,看镂空的屏风上光影陆离,喜盈盈可握的茶杯里云影徘徊,只觉得,连屋子里的空气都是透明的,如梦如幻,定是经了茶席上那朵莲香的过滤。
只是一朵莲花啊,在茶席的一角斜斜伸过来,每一片花瓣都有各自的韵致,如拈花的手指。跟随一朵花开,给自己一盏茶的时间,在低眉垂首之间,放下我执,回归本心,是多么优雅自在的事。莲花入心,时来已久,与那张茶桌上的草席,却是此生初见。草席用那种细细密密的草梗儿精心编织而成,和茶盏下的杯垫呼应着。我看看杯垫,又看看茶席,眼前幻化的是细细的麦浪,麦浪上闪耀着金子般的阳光,陶杯里晚霞潋滟,是一杯普洱茶,茶汤暖暖的,香醇绵久。几个女子说到兴头上,不由得花枝乱颤,带着眼镜的冷美人,却原来有一副温热的软心肠,那个快言快语的女子,手指起落之间,竟尽显女儿情态,茶室主人正轻启红唇,娓娓而谈,说美食,说手工,说太极,说摄影,说她正热衷的习茶,说下一步的经营计划,如是美人,娴静如临花照水,让人倾心的不是温柔妩媚,而是一颗学子心。低头呡茶,茶汤入口,有点软,有点甜,不急不躁,刚刚好,仿佛入心的话语。其实,人与人最初的相知,许是一句熨帖的话,一声切切的唤,一抹甜美的笑,在一瞬间打开了我们情感的密码,于是一念倾心,从此痴痴缠缠不离不弃。
突然,啪的一声,扭头寻时,一粒莲子正从干枯的莲蓬里滚落在地,心里陡然一惊,想起那句“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诗句,可这是莲子,不是松子,这是斗室,不是空山,想起盛夏的莲池里,莲蓬青青,饱满的莲子一粒一粒,嵌在圆圆的莲蓬之中,如密密麻麻的心事,莲子清如水,说的是“怜子情如水”啊,一份蓬勃葱郁的情怀,自弄莲的女子心底徐徐飘散,直到染绿了山水,惊艳了一世。

要经历多少风霜,才可修炼一份澄澈宁静的秋水之心?那水,盛在小小的茶杯里,不起微澜,都是四十岁开外的女人了,谁没有起伏跌宕哭过笑过,只是不说罢了。茶汤绿意盈盈,定是想起了一段少年心事,水中泛起金黄,定是倒映着那年的甜言蜜语,眼见着水中升起暮色,所有的过往,无论欢欣还是悲苦,百般滋味,都会沉淀成一股令人回味的清气,品人生百味,润着肺,洗着心,直到两胁之下,习习生风,我欲乘风归去。身未动,心已远,茶入衷肠,其实是借着一片叶子,漂洋过海,超度自己。
茶韵悠悠,不禁想起邻城的姐姐,性情如水,韵致如茶,我们之间,虽然相隔不远却很少遇见,只是每天都能在微信里知道她正读什么诗,她会在黄昏的街市,买下跛脚老人的无花果,那些粘着泥土的蔬菜,也许品相不太好,但她想让老人早点回家。暮色四起的路上,她忽然停了车,默默看着那个清洁工挥舞着扫帚,载歌载舞,突然泪流满面……这份慈悲,我懂得,这样的文字,忽然就触动了内心柔软的弦,那些情景历历在目,仿佛亲为。我深信,抵达心灵的最快捷方式,是文字里的相知,姐姐的文字读多了,就觉出一种心心相印的欢喜来。忽然想起很久没去看望那个80多岁的老人了,她孤身一人临水而居,每天忙着做缝纫,忙着把做好的手工送给需要的陌生人,她不懂佛法,却在做着佛的善事。我喜欢这样的人,她们是带着光辉的人,心如明镜,能照见世间所有的美好,我总是被她们吸引着,也努力简单而快乐地活着。
与茶友说笑之余,左顾右盼,褐色的莲蓬或悬于廊柱,或插在瓶中,高低俯仰,自在天真,木架上的瓷罐上也有一支莲花正摇曳生姿,一屋子的美人,言笑晏晏,仿若朵朵莲开,在这样的境界里,我轻轻端起莲花杯,想起那首“愿做佛前那朵莲”:
愿做菩萨那朵莲
修炼心法永无杂念
花开花落在你身边
做前世今生的水莲
……
摘自2016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周霞(山东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