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当下成为一个热词,乡建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建筑学展现出的一个新挑战。在过去几十年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化建设中,全国各地的城市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现象。如今,全球化、现代化浪潮正无可避免地从城市向乡村席卷而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理解传统?在城乡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下如何安置传统乡土建筑?在巨变中的当代乡村将以何留住乡愁?202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茶村生计—一个福建茶村的空间与社会变迁》[1]一书,试图以一个“地区建筑学”[2]范例去回应处于新时代背景下的乡建所面临的困境。

该书是作者黄华青是在地区建筑学研究路径下,对中国当代乡村建设研究所开展的一次可贵探索,通过对武夷山G村当代乡土建筑开展田野调查,研究当地在茶产业发展影响下的空间与社会变迁。作者通过对25座厂宅空间的“深描”和165个厂宅样本进行梳理,提取产业量化因子,并建立起可视化图表模型,由此归纳出G村于当代所形成的“宅”“厂”“店”三位一体的乡土建筑模式,即融家庭、生产和经营空间多功能于一体的“厂宅”空间模式。其中,不同时代茶产业发展的需求是推动空间变迁的主导因子。
全书共7章,第一、第二章为田野点铺陈和方法论介绍,第三至第六章为全书主体分析,第七章为结论。第三章历时性展现出武夷山茶村空间结构及G村厂宅空间模式在全球茶叶贸易和地方制度变迁中的成型和重建过程。第四章从地方社会结构层面出发,探讨茶农“身份”认知变化给当代家庭关系造成的变化,以及对家庭空间结构的重构。第五章以“技艺”变迁为线索,探讨以菁楼为代表的传统生产空间与现代茶厂生产空间之间的斗争与调适。第六章进一步追问随茶旅经济而产生的“他者”凝视对当地建筑风格的符号化[3]影响,并从空间符号化现象切入,研究茶村社区分化现象及其在厂宅经营空间上的表征。第七章中,作者总结G村的“宅”“厂”“店”3种建筑基本语素于3个历史时期的贯穿交融,并在此基础上对“何为传统”进行反思。

从观察视角来看,作者首先从地方史与世界史“内外交织”的大历史角度出发,将G村这一小茶村的空间结构变迁置于宏大的近代全球茶叶贸易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及当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脉络中进行分析;又以微观视角进入建筑空间内部,观察在商品经济和茶旅发展的影响下,G村民家中正在发生的“堂屋茶室化”“卧室宾馆化”等空间功能转向现象,以及新的“厂宅”空间与传统的家庭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作者身为建筑学博士,在方法论上却深受人类学影响,将地志学引入建筑学研究,并在“地势民族志”[4]的启发下引出“空间志”这一研究路径,作者称之为“spatialethnography”(空间民族志)[1]。将“空间志”作为全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试图从主客一体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景观、空间的时间维度3个层面出发,探索一条沟通物质与感知、精英与大众、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路径。

空间志方法对建筑学领域的一大显著贡献是:实现了建筑学从传统的静态视角向动态视角的转变。“针对乡土建筑学者所面对的乡土建筑研究对象,主张关注空间的本质—不断变化、消亡、重建的空间。其中作为主体的使用者和作为客体的物质空间、作为文本的建筑空间和作为非文本的建造及栖居过程都是动态性的”[1]。这一研究在瞬息万变、乡土建筑不断陷入“拆—建”循坏怪圈的当下农村社会尤显重要。与一般的人类学民族志相比,该书提出的“空间志”在文本呈现上体现了建筑学的学科优势:在描述房屋空间的文字旁,基本都附有作者实地测绘的“建筑空间结构图”,令人一目了然。社科学者在讨论“空间”议题时,往往会因拙于绘图而使论证乏力,该书恰恰弥补了社科领域“空间研究”在文本呈现上的不足,令读者常有“一图胜千言”之感。如第五章“菁楼中的传统技艺空间模式”,通过图示清晰地展现出菁楼各层在萎凋、捻揉、发酵、熏焙环节中的具体功能,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菁楼“高效、合作、劳作”的特点。
“空间志”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对社会空间概念的引入,从而使该书对G村空间变迁观察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房屋空间结构下的人伦亲属关系[5]成为作者“凝视”茶村的重要着眼点。作者对乡贤的精英社交、茶农的茶室营建、兄弟之间的分家与新家修建的描绘,生动地向读者展示出新的伦理观、社交原则、阶层分化等对村落景观和村落空间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出空间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6]。例如第四章对潭溪洲胡氏大家族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家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大家族的分家过程不仅影响兄弟间的新宅营建分布,甚至主导着其所在自然村的形态变迁。通过对比潭溪洲三代村落空间布局图,明显可见自然村的代际空间拓展受到分家影响,村落的空间增长也反映出大家族的继嗣与裂变。

“原真性”[7]这一在建筑学、国际遗产保护、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引起广泛讨论的概念,成为该书分析和反思“传统”的一个关键词。作者对“原真性”的思考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1)作者对茶叶产品的原真性的诘问。关于茶叶的“原真性”判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是“风土”和“技艺”,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地理原真性”和“技术原真性”两个范畴。对“地理原真性”的区分,使G村的空间产生“正山/外山”的空间划分[8]。但现实情况却是,由于正山茶青成本过高,“地理原真性”往往被当地大茶企把持。而大量涌入G村的“外山”茶青,虽缺乏“地理原真性”,却通过当地中小茶企代工,甚至通过利用G村的菁楼进行加工,而拥有了“技术原真性”。对这类没有正山“风土”,却拥有正山“技艺”的外山小种是“排斥”还是“接纳”,也成为当地茶农面临的两难选择,结果导致在同一茶企的建筑空间内产生“内/外”两分制。这种“内/外”区分一方面可被解释为自然环境上的“正山/外山”区分在建筑空间上的体现;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当代商品经济浪潮对乡村自然空间挤压的结果。
(2)作者对地方建筑原真性的诘问。作者大胆引入符号理论,揭示了当代乡村“建筑风格”从“超真实”到“现实真实”的动态裂变过程[3]。如果将传统乡土建筑视为“破败的真实”,那么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由建筑师设计和乡贤精英们引领的“现代乡土”建筑则是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而如今普通村民自发大量拙劣模仿的“新乡土”建筑则正成为当代乡村的“现实真实”(real-reality)。作者将当地乡土建筑风格的演变史置于G村的茶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试图去区分理解这些“风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产生的意涵,从而揭示了从“超真实”到“现实真实”的乡建风格迷局。

对武夷山制茶历史的探究虽非该书作者的主要研究目标,但相较于一般历史学者而言,作者特殊的知识背景结构,恰恰弥补了中文材料阙如造成的研究困难。通过对菁楼的物质文化进行考察,力图还原武夷山的红茶加工历史是该书“无心插柳”的一大贡献。以往对菁楼历史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当地茶农的口述历史,但作者通过对波尔(Ball)笔下19世纪初期星村周围的萎凋棚与同时期印度北部的大型萎凋楼进行对比,以及对使用中的菁楼在制茶各环节的功能进行实地田野考察,认为菁楼并不像当地茶企宣称的那样“见证正山小种红茶400余年的发展历史”,而极有可能是受到印度、锡兰等英国殖民地的大型茶厂影响下的“现代化产物”,最终成型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中。
吊诡的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以“协作”和“高效”为特点的菁楼在以家户为制茶单位的今天却显得“大而无当”,尤其对小规模生产者而言,菁楼因“耗材”过高已经失去了实际使用价值,而成为企业产品宣传中一种象征“传统”的符号。但除了表面的“布景”作用,作者更为敏锐地指出,菁楼存在的建筑“合法性”(legitimacy)还在于其持续的社会性价值。“菁楼这个不可取代的、经过亲身的度量和肌肤的热感所体验的空间,赋予了茶农和品茶者一种独特的优越感。这种空间中的劳作,而非表面化的空间或材料布景,才是菁楼这一技艺空间的内核”。作者将主观的感官经验加入对菁楼的物质文化[9-10]考察当中,从而超越了一般建筑学意义上对“空间”的测量。正是这种“体物入微”的“进入”到空间中的研究,才能体察到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织与建构[11]。

该书稍显遗憾之处是:对当地茶农的身份转变分析缺乏对相应的“类型研究”的回应,从而局限了该书的研究贡献。武夷山的山区经济不同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地主”关系,当地几百年以来一直就以经济作物(cashcrop)生产为主,较早进入市场交换体系,且在17—19世纪达到高峰,被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民国”时期,武夷山就出现了包头、岩主、带山、制茶工、采茶工等高度发达的行业工种划分,种田者反而极少。因此,在家庭经济收入高度依赖于市场的武夷山区,并不适合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农民”身份出发去理解这种复杂的内部关系。笔者认为,当地茶农与茶工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由传统互惠式道义经济(moraleconomy)向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转变,而是有迹可循,植根于当地原本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历史脉络之中。作者虽在该书中对武夷山“茶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转换进行了相应探讨,但仍较局限于“农民”这一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G村的部分“茶农”转变为领取工资的国家“工人”,这显然不同于绝大多数农村,如作者能再加强对G村地区的差异化分析,或许可为读者理解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另类乡土中国[4]提供一个范本。
“他者的凝视”正在成为塑造当代乡村建筑风格的动力马达,这种“凝视”并非同一水平线上的“互视结构”,而是一种城市资本高高在上的非对称结构,也是一种知识权力的生产过程。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由发达国家消费端所构筑的“第三世界农业幻想”[12]进一步加深了农产品原产地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为满足城市精英们的乡土(vernacular)幻想,村民们不得不对其生活的空间进行一系列的传统“包装”,从而导致当代乡村建筑风格的“乱象”。

在该书结尾,作者针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现状提出了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连问和反思:我们正在保护和建构的是怎样的传统?是何时的传统?又是谁的传统?对于这3个问题显然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功经验可以照搬。但作者通过该书对“空间志”与“地区建筑学”进行结合研究,提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建筑学者对当代乡村,尤其是对各种号称回归“传统”的乡村营建的反思。“地区性是建筑的根本属性之一”,“空间志”强调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传统”,唯有将此二者结合,才有可能获得建立在本土文化自信之上的真实传统,而非从他乡借来的乡愁,而这也正是当下全国各地在“美丽乡村”建设热中应有的“冷思考”。
“夫沧桑变迁,则有终归无;而文字以久其传,则无可为有”。在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G村的乡土建筑再过10年应又是另一番模样。这正如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并不意外地发现,10年前一位当地精英向笔者描绘的自家“徽派建筑”规划已然成为该书中描绘的现实。《茶村生计》一书以文本的“历时性穿梭”为读者留下了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当代G村乡土建筑范式。而终有一天,这一“纸上G村”也将成为被后来者继续拷问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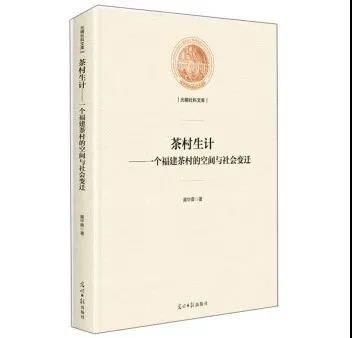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黄华青,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先后获得建筑学学士、工学博士学位。2017年至今在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从事传统聚落及其当代变迁研究,曾赴米兰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巴黎伦佐·皮亚诺事务所实习半年,足迹遍布欧洲及世界各地30余国,广泛考察经典城镇及建筑。
参考文献
[1]黄华青,茶村生计:一个福建茶村的空间与社会变迁[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0.
[2]单军,建筑与城市的地区性:一种人居环境理念的地区建筑学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M].FLASERSF,Trans.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94.
[4]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6]LEFEBVRE.H.Theproductionofspace:Vol.142[M].DONALDNS,Trans.Oxford:Blackwell,1991.
[7]MACCANNELLD.Thetourist:anewtheoryoftheleisureclass[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13.
[8]肖坤冰.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BOURDIEUP.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M].RICHARDN,Tran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4.
[11]INGOLDT.Theperceptionoftheenvironment:essaysonlivelihood,dwellingandskill[M].London,NewYork:Routledge,2000.
[12]萨拉·贝斯基.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M].黄华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来源:坤冰观茶
文章来源:《自然与文化研究遗产》,2020年4月第5卷第2期,Pp143-146。












暂无评论